骨脈相傳 蔚然成林
撰文‧黃秀花 攝影‧顏霖沼
 |
花蓮慈院三十周年院慶大會,陳英和(左三)與資深同仁上臺領取模仿本尊製作的公仔;三十年也等同是他服務年資。
|
三十年前,
陳英和成為花蓮慈濟醫院首位報到的醫師;
將在臺大醫院所學淋漓發揮,
更創新術式,
成為「骨科變形矯正」專家。
他傳承給學生的不只是醫術,更是態度,
「醫師不該圖輕鬆而拒絕難治的病患,
而是要承受壓力,
努力想怎麼做最好,想得通就做下去,
病患的生命就有機會改觀。」
圓潤臉頰、面露光澤,生就一張娃娃臉,唯在思考問題時,會見其眉頭緊蹙、紋路隱然浮現……這位年過六旬的男人,歲月並沒在臉上留下太多刻痕,髮絲也僅幾縷翻白,看起來較實際年輕,但又不失成熟與智慧——他就是花蓮慈濟醫院前院長、現為名譽院長的陳英和。
花蓮慈院啟業以來,他是第一位自願報到服務的醫師,一待三十年;他精進於骨科專業,醫術和醫德皆為病人所稱頌;他樂於提攜後進,慈濟體系六家醫院都有他的子弟兵,甚至散見外院。
親炙他二十餘年、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簡瑞騰說:「陳院長是我的恩師,最尊敬的老師;很榮幸能當他的學生,從他身上不僅學到了技藝,更學得『承擔』與『責任』,一輩子受用。」
師傳徒,本就是醫學進步的原動力。陳英和的無私、以病為師、研究創新精神,將醫師角色詮釋得淋漓盡致。身為一位醫者,他認真對治疾病、實事求是;作為一位老師,他善於發掘學生長處,樂見弟子青出於藍;泱泱大度襟懷,銜含著是一分使命,也是為了傳承。
來花蓮搶時間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十二歲、還是臺大第五年住院醫師的陳英和,落腳花蓮。問起他當年哪來的勇氣,敢投身一家未知的新興醫院?他說:「從進入醫學院,一路成長到當住院醫師,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希望發揮所長;所以做這個決定,並不『沈重』,也沒有『取捨』的關卡。」
三十年前的花蓮,不若今日人人想來觀光,反而像是「化外之地」,除了原本住民,移民多半是在西部難以討生活,才東來尋機會;花東醫療水準落後西部一大截,民眾生了重病,不是往北就是往南送,生命常因此延誤……
到了花蓮,陳英和很感恩劉堂桂、陳博光、陳楷模等幾位教授,幫他打了很好的底。「老師們所教,足夠應付花東病例的百分之七、八十,另外百分之二十屬於疑難雜症,就要靠自己摸索。」
陳英和是很用功的學生,住院醫師前兩年以神經、胸腔、整形及一般外科訓練為主,也輪派到急診、加護病房、麻醉科等重症單位學習,因此外科基礎訓練很紮實,後三年,才全力朝向他喜愛的骨科(Orthopedics)受訓。
住院醫師最後一年時,他已決意要來慈院,自知責任重大,很努力把現代骨科醫學的每一部分,如骨折接合、脊椎修復、關節置換、骨腫瘤等手術都鑽研透徹,希望東來後能照顧各種骨科病人,不必再後送。
這當中也包含精密的顯微手術技能。最初慈院還沒有整形外科醫師時,所有接斷指工作,都由他一肩扛起,直到第三年,整形外科簡守信和骨科謝沿淮兩位醫師才加入行列。
講到此,陳英和不免苦笑:「骨科醫師向來習慣大動作做切、敲、鑽、拉手術,要靜如處子慢慢細針做切、縫,真是一件苦差事。」但他勉力而為,「因為其他病症都還有時間可轉送去西部醫治,唯獨接斷肢和斷指需要搶時間,不立刻接回,就會耽誤病人一生,豈能不戒慎!」
一九八七年,十四歲少年林傳欽在一場意外中被大理石壓斷雙腿,送到花蓮慈院;外科主任張耀仁和骨科主任陳英和等醫師緊急搶救,後來為了避免傷口繼續感染惡化引發敗血症,不得不施行高位截肢手術。
林傳欽截肢後,以移植皮覆蓋傷口,非常脆弱,卻要承載他上身重量,實在有困難;陳英和思考:「什麼是比軟墊坐起來更沒有壓力,不會傷到薄皮呢?」他想到是「空氣」,再想如何裝進去?就是「氣球」,從而他當晚回家就很認真吹氣球,恰巧父親從高雄來小住,看到一個大男人做這動作,還以為他「童心未泯」;實則他是為病患著想,希望林傳欽趕快坐起來復健。
 |
慈院啟業初期,與臺大醫院建教合作,多位教授級醫師也親自支援看診或手術;陳英和(最後排左一)的恩師劉堂桂(前排左四)、陳楷模(左五),傳承給他醫術與醫德。
(相片提供/陳英和)
|
隨時檢視初心
一九八八年,陳英和遇到先天性髖關節脫臼的病人。那名婦人三十多歲,年輕時,假性關節猶能使用,但隨著歲數增長,不能站和走,骨頭會痠痛;一般處置是更換人工髖關節,但婦人屬於高位脫臼,大腿骨跑得太高、髖臼很低,高低落差七公分;若把人工股骨柄放上去,硬拉髖臼上來做連接,旁邊的神經會麻痺壞死。
陳英和思索良久,決定先截斷大腿骨的股骨中段,切除五公分,再挑選合適的人工髖關節置放;此項「以股骨縮短及全人工髖關節置換術」難度很高,但術後就讓婦人能恢復行動。這種創新的人工關節置換手術,在臺灣算是首發,對一位年輕醫師而言,無疑自信和膽量倍增。
一九九一年,更嚴重的僵直性脊椎炎導致駝背的張女士上門求助;她脊椎變形和硬化程度已非單純術式可處理,外觀異於常人,也使她自卑封閉。
當時,陳英和已經知道「切骨矯正手術(Pedicle Subtraction Osteotomy)」問世,但別說在臺灣沒人開過,香港也僅止於個案報告階段。對於這麼艱難的案例,是否該承接?他想及醫師守則有一條「Do no harm」,意即不能傷害病人;但反覆考量,覺得自己所具備的技術,足以應付:「若我能開,病人的生命就能為之改觀。即使沒有達到理想,也會比原來好一些。」他和張女士溝通,張女士決定接受手術。
手術前,他仔細思量:「能做到什麼程度?會碰到哪些問題?」他繪製分解動作圖解析,模擬演練,確認慮及所有環節,已然胸有成竹,才敢大膽下刀。結果,手術順利完成,張女士終於能抬頭挺胸,直眼視人;這就是陳英和所做的第一例「經椎弓切骨矯正術」。
接著,陸續有病人聞風而至,第四例患者、來自南投的曾先生,脊椎彎度達一百四十度;陳英和為他進行三階段手術,讓他可直立,此例也破了文獻所載的矯正度數,引起媒體大幅刊登。從此又有更多遠地和國外病人求診,那七、八年間,是陳英和執行相關術式的尖峰期,技術日益純熟。
而在與病人互動中,他感受到:「其實他們的心願都很卑微,有的只期望開完刀後能平躺,而不是只能側睡;有的是希望能抬頭看人,視角不再往後垂;甚至有人會說,在他大限來臨時,至少要能擺得進去……」因此,再困難的個案,陳英和都會努力克服,想得通,就能做下去。
曾先生曾經彎駝到連肚皮都看不見,在矯正成功後幾年,不幸罹患胃穿孔;還好先前已經拉直脊椎,才能及時施行手術救命,不然連開刀的機會都沒有。
 |
大林慈院簡瑞騰副院長是陳英和的得意門生,改善阿吉伯的嚴重病情。他學到老師的骨科手術技巧,以及對病人的責任與承擔。
|
陳英和腳踏實地,認真執行每一例手術;遇有超乎經驗的病例,他就想方設法。「在臺大拜師學藝,我不只學到『術』,還有『德』。」師承臺大幾位骨外科先進的陳英和,謹遵師長們教誨,特別骨科劉堂桂教授最注重標準做法,他常講「Orthodox」──此字取自東正教,是蘇俄、東歐一帶慣用語,意思是「正」,無論是用在臨床手術或為人處事上都很貼切。
老師的行為準則,無形中影響了陳英和,受用至今。「當醫師有太多機會可拿到一些利益,但這些是不正、不應該的。」陳英和說,身為醫師,「正直的純心」非常重要,思想要純正,不能有絲毫偏差;且也不該圖輕鬆而拒絕難治的病患。但承接病患的同時,必須確認自己動機純正,「不是為了自我功成名就,更不能為了個人目的,給予病人不必要的醫療。」
態度代代相傳
「我這位老師是術前有準備,術中留迴旋退路,術後用心照顧。」師學陳英和的簡瑞騰,在住院醫師第一年就來到花蓮慈院,幾年內密集跟隨陳英和上刀,學到的不僅是開刀技法,還包括為人處世、醫病關係。
簡瑞騰一九九○年退伍,到臺大醫院應徵骨科住院醫師,劉堂桂教授發現他是嘉義大林人,建議他到花蓮慈濟,學成後可回鄉服務。當時也是陳英和為僵直性脊椎炎患者執行變形矯正手術最頻繁的時期,簡瑞騰一檯接一檯刀跟;自一九九一年起,經歷過六、七十例手術,他說老師都是一本初衷──術前做好計畫,術中尋求配套方式,特別是矯枉要過正,以及術後何時可負重和復健,都已在陳英和腦海中盤旋過好幾回了。
所謂「矯枉要過正」,也是劉堂桂教授所教,手術時要「Over Correction」。陳英和從臨床上印證,譬如骨頭變形八度,就要矯正十度,因病患已習慣那種彎度,矯正後可能會再回來一點,所以要保留「回縮」空間。
陳英和謹慎要求所有環節,近乎神經質;因為他認為醫療過程有很多不可預測,儘管已經很小心處理,事前多一分準備,碰到意外狀況時,就能減少病人受傷害的機會。也由於每例手術都是在反覆確認中進行,團隊壓力相當大;難怪簡瑞騰要以「刻骨銘心」來表達師徒們所共同的經歷。
簡瑞騰覺得跟刀最驚心動魄之刻,是每當老師把病人的脊椎骨切到快斷掉,此時神經和大血管易受影響,現場一片鴉雀無聲,直至聽到「喀」一聲,他們在旁邊擔任助手的幾位,便要趕緊把病患的身體「扳直」,老師也會問麻醉科醫師,神經監測器的波動有無很強烈?若有,就要他們再放回去一點,確定無誤後,才進行下個動作。
術後,等病人在恢復室甦醒,陳英和又會去測試他的腳能否自主擺動,若看到能動、血流也順暢,他才會微笑地揚長而去,代表手術是真正成功。
後來,師徒倆蒐集整理多年案例,將珍貴的資料和術式經驗撰寫成論文,於二○○一年發表於國際期刊。
二○○五年,這篇論文被美國《骨科新知》(Orthopedic Knowledge)引為第八章節主要內容,也是臺灣骨科專科醫師考試必讀考本;二○○九年,陳英和還獲美國《小兒脊椎手術》教科書之邀,寫成篇章分享手術技法。原本艱深冷門的手術,逐漸在國際骨科學界為人所知。
「他不僅是臺灣之光,更是慈濟之光。」簡瑞騰感謝恩師陳英和願意傾囊相授,讓他也學會執行這麼高難度的手術;其中,他做過最嚴重的病患阿吉伯,頸椎脫位、神經壓迫、眼睛睜不開、舌頭吐出、呼吸困難等;由於阿吉伯住在臺南,陳英和推薦他就近到大林讓簡瑞騰治療。
「我知道他可以,絕對能勝任,所以放心把病人交給他。」陳英和對於初任大林慈院骨科主任的簡瑞騰很有信心,只是從旁協助擬定治療計畫。
這是慈院骨科醫師首次在花蓮以外開僵直性脊椎炎手術,簡瑞騰做得很成功,加上志工團隊的照顧,「阿吉伯」術後身體和心理都得到大幅改善。
抬頭挺胸邁大步 醫師好骨力
經椎弓切骨矯正術是陳英和所獨創,手術已逾兩百例,近年來求醫個案複雜度更高。大陸廈門楊曉東軀體變形兩百度,陳團治是罕見雙膝反曲患者,陳英和術前充分準備、術中小心對治、術後用心照顧。兩年後,陳英和去大陸探望楊曉東,他已能騎單車載陳英和,醫病之間的喜悅溢於言表。
陳英和也是翻轉陳團治命運的貴人,彼此猶如父女,為她選購復健鞋,親自試穿矯正鞋感受,教她術後如何開步走;而團治也不負期望,走出亮麗人生,也學習當志工助人。(相片提供╱花蓮慈院)
甘願「緊張兮兮」
六十二歲的陳英和,不斷保持前進,不以現況為滿足。近幾年就分別接了兩大艱深病例──楊曉東是肢體嚴重扭曲的僵直性脊椎炎病人,脊椎加髖關節變形超過兩百度;陳團治是先天性極重度雙膝反曲,雙腳呈L型,只能靠膝蓋後側的膝膕窩艱難跪行,全球罕見。
兩例難度均勝於以往。陳英和針對陳團治的治療,在膝關節處是結合「閉鎖式」和「開放式」兩種切骨矯正手法,使其達到一百六十度的高矯正量;針對踝骨部位,因為她的足掌形同馬蹄足往下垂,必須同時間進行踝關節的切骨扳正及後跟腱的「Z」型延長;但延長後,原有韌帶會「細若游絲」,故要先切開,取來異體韌帶做補強,每個步驟的分寸拿捏十分謹慎。
「我看到院長做每個動作都小心翼翼、步步為營。」跟著陳英和進行這兩例手術的花蓮慈濟醫院骨科醫師劉冠麟說,老師已是大師等級,但對待病症和病人卻很謙卑。
陳英和率領團隊歷經多次手術,最終讓兩人身體打直,站起來走路。他說,接這麼困難的刀,壓力絕對有;如果他怕困難、怕辛苦而拒絕了,對病人就很不公平。但接了後,卻也令他成天「緊張兮兮」,幾乎從病患住院起,排定手術、開刀、術後照顧,「每晚入睡前想的最後一件事,及清醒後想的第一件事,都是『病人』。」
這習慣,陳英和從以前一直維持迄今;經他治療過的重症病患,叫什麼名字、家住哪裏、住院時是幾號病房、床位靠窗或門口……他都記得清清楚楚。
其中,針對陳團治這個雙足變形的女孩,陳英和不是為她動完手術就算了,還考慮到她術後的生活及復健。為了讓她明瞭之後走路的模樣,他穿上在關節處鎖緊的矯正鞋,模擬其關節僵硬、活動被限縮下,如何行走給她看。當他在爬樓梯時,女孩在後面笑了出來,那是醫病間的真誠相待,也詮釋了什麼是「全人醫療」。
只是,他善待病人,卻苦了家人。在醫院時間一多,在家時間就少,回到家也無法放鬆;太太總用「無趣」調侃他,媽媽則心疼地說:「你都六十幾歲了,還那麼拚!」儘管如此,家人始終支持他在專業領域精進。
 |
陳英和傾囊相授,子弟兵散見六家慈院與外院。他不藏私,泱泱大度襟懷受人敬重。
|
醫者社會責任
陳英和認為,三十多年前受教於臺大多位恩師培育,才有如今局面,而他更期望學生後輩能超越自己,「教學相長」一直是他所倡導:「老師並不一定每樣都勝過學生;同理,學生也不必自我侷限,有很好的發想和創意手術,照樣能贏過老師。」
臺北慈院骨科醫師曾效祖在觀摩過陳英和的「經椎弓切骨矯正術」後,今年七月在花蓮慈院執行一例三百六十度環椎切骨術,這是最近十年來發展出的新術式,難度非常高,專門處理嚴重的駝背變形。
陳英和極為讚賞,特別是這種手術非常辛苦,往往從清晨開到半夜,而且手術全程需要神經監視器,神經外科技術團隊得通宵達旦支援。花蓮慈院是少數能夠提供這樣強力支援的醫院,讓他無後顧之憂進行手術。「目前臺灣唯一能做這種手術的只有他,那天是他的第九例。我也沒做過,他給了我們骨科團隊很好的學習機會。」陳英和說。
全臺每年規畫給骨科的住院醫師只有五十幾人,各大型醫院需求殷切,花蓮慈濟醫院骨科訓練環境受肯定,一年可以爭取到兩個名額。陳英和細數,歷年培養出的優秀骨科醫師,已經開枝散葉到各所慈院——
簡瑞騰在大林,已是開脊椎手術的一把好手;花蓮慈院的吳文田,頸椎手術技法精良;在關山慈院擔任院長的潘永謙,不論開刀或管理都有獨到之處;派駐玉里慈院的林志晏,是守護當地的一道門;臺北慈院的黃盟仁,專精於小兒骨科;曾效祖醫師則被他讚譽為青出於藍。臺中慈院陳世豪醫師過往雖然不同體系,但每週二來花蓮教學時,也會加入骨科病例討論。
「我不覺得自己老了,也不覺得工作勞累、想要退休,但職業的年限終會結束,我對『傳承』有急迫感。」陳英和說,身為一位醫者,做好傳承很重要,團隊才會進步,受惠的是整個社會人群。
四年多前,他也在臺大景福館創辦「脊椎晨會」,以慈濟擅長的「變形矯正」為主,透過病案討論彼此交流、提升技能,參加者包括臺大、榮總、長庚及慈濟的骨科醫師,毫不藏私地分享同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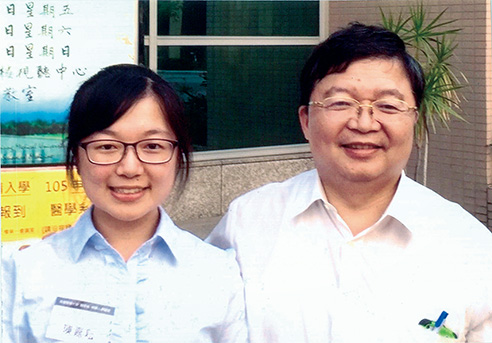 |
陳英和的次女陳嘉耘今年考上北醫醫學系,陳英和喜見家中有人傳續醫師志業。(相片提供/陳英和)
|
在學生簡瑞騰的心目中,陳英和就像「巨人」,謙遜不刻意露鋒芒,但真的有需要,他也會抱定「雖千萬人吾往矣」,認真去做事。就像一九九九年,花蓮慈院為了申請升格醫學中心,他自覺是資深醫師能起帶頭作用,便戮力承接起「院長」職務,帶領大家往前衝;又如角逐骨科醫學會理事長,是孚眾望所託,希望有所作為及付出。
還有一點,讓簡瑞騰最感佩服:「陳院長很尊師重道,只要跟從前教過他的教授走在一起,必定會幫對方提包包。」他還說,老師對於生長環境念念不忘,其內公和外公各為嘉義和雲林人,所以便將次女取名為「嘉耘」,只是將「雲」轉成諧音的「耘」,就希望女兒腳踏實地、認真耕耘。而嘉耘也不負期望,今年以七十四級分錄取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傳續老爸的「醫師」志業。
幼年成長於雲嘉南鄉間的陳英和,父親是過去臺南永康糖廠員工,母親是小學老師,醫業承襲母系外公之一脈,這樣的綜合背景,讓陳英和對弱勢民眾特有感受。他在花蓮行醫三十年、每週兩日到臺北慈院駐診和開刀也十一年了,發現到此兩地異鄉客很多。看診時,每遇身分證字號是「P」開頭,就知道對方來自最窮之縣雲林,他總會對長輩多關心幾句:「您是特地上來看診,還是孩子住在這裏?」
對於後進,他則多所提攜,並以「教練」自勉:「一個教練在運動場上的表現,會強過學生嗎?」這顯然是他謙虛之詞,但卻強調要憑藉個人的無私和號召力,將團隊帶得更強更合心。
「不要小看自己,人有無限的可能!」這是陳英和最喜歡的《靜思語》,正因深信如此,他認為每個人的出現,都是上天的恩典,在適當機遇下,都能發光發熱,都可能是人群之「寶」,這是他對待學生的基本態度。
以此他也常檢視自我,要「莫忘初衷」,當初因緣際會來到花蓮,日久了,他鄉也變成故鄉,心早已跟這塊土地黏在一塊。就如他常掛在嘴上的一段話:「要說我當初為何會過來,倒不如問我為何沒離去!」這一念初發心,陳英和永遠沒改變。

|



